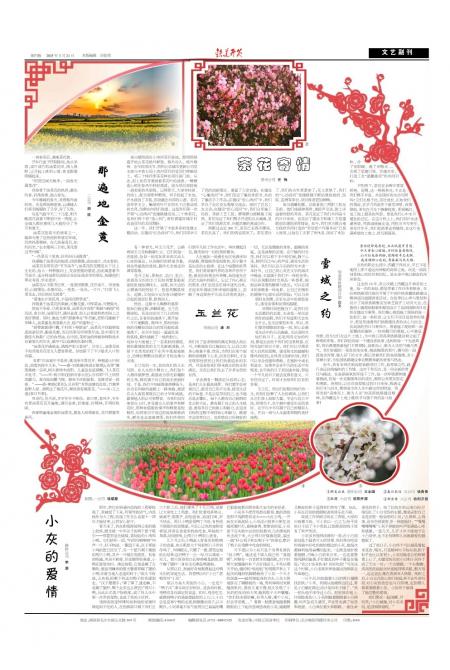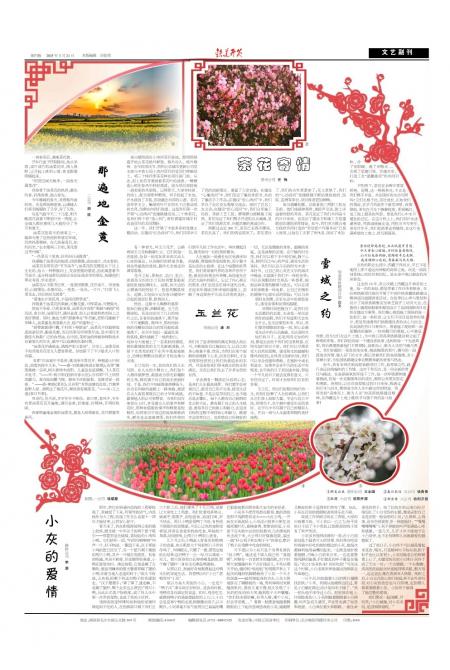
A4版:文艺副刊
小灰的爱情
刊发日期:2025-03-21 阅读次数: 作者:
路桥公司 李漫
那年,单位在昭通内昆线的工程要收尾了,我被留了下来,听领导的语气,内昆线作为大工程,收尾工作怎么也要个一两年才能结束,让我安心驻守。
春天来了,我在距指挥部两公里的镇上赶场,眼光被一中年汉子的两个筐子吸引——那筐里是毛绒绒、黄灿灿的小鸡和小鸭,它们挤作一团,“叽叽叽啾啾啾”叫声一片,好不热闹。一圈逛下来,汉子那装小鸡的筐已经空了,另一个筐只剩下瘦弱的两只小鸭,其中一只缩在角落里。初春的昭通,风虽不刺骨,但也颇带些寒意,小鸭在瑟瑟发抖。凑近细看,它竟是瘸了左脚的。假装用嫌弃的眼光瞥着那瘸了腿的小鸭,学着当地人老道的样子:“收头不收尾,五块钱,把剩下的这对鸭子给我逮到走。”汉子摆摆手:“算了算了,逮走嘛,不是瘸了腿杆,哪个会卖这么便宜!”两只小鸭,从此正式落户指挥部,成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养的宠物,也成了我的小伙伴。
指挥部饭堂师傅何叔和他的家属何婶是闲不住的人,在指挥部只剩下我们五六个职工后,他们便养了十几只鸡,说要让大家吃上土鸡蛋。鸡们仗着鸡多势众,威威乎,荡荡乎,到处刨食,追逐打闹,好不快活。两只小鸭显得鸭丁不旺,有些找不到组织的恐慌感。不忍心让我的宠物受委屈,我常在食堂里找些吃食,单独找个角落,站岗放哨,让两只小鸭安心进食。
几个月之后,小鸭进入青春发育期,鸭子的食量、块头明显大于何叔两口子养的母鸡了。何婶眼尖,只瞟了一眼,便笃定地给出结果:这对鸭子一公一母,可以凑成一对儿,那只浑身雪白长得乖嘞是新郎,那个瘸了腿杆一身灰毛毛嘞是鸭婆娘。
从那以后,我就好奇地观察起这对鸭夫妇的家庭生活。我管鸭公叫“小白”,管鸭母叫“小灰”。
原以为高大英俊的小白,一定是个“鸭子汉”,事实却正好相反。觅食的时候,鸡鸭有各自固定的食盆。有时,鸡先吃完,就摸到鸭子的地盘想趁机叨上几口。小白总是息事宁鸭的态度,稍微挪动身子,以示默许,小灰则毫不客气地用自己扁扁的嘴巴狠狠地教训那些胆大妄为的来犯者。
小灰并不把母鸡放在眼里,她的劲敌是那只鸡群里的老大——大红公鸡。一开始在正面战场上,小灰没占到多少便宜,但她死缠烂打,愈挫愈勇。更要命的是,小灰善于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几次漂亮的伏击战下来,大公鸡只好偃旗息鼓,装出一副“好公鸡不和女鸭子斗”的姿态,默许了鸭子在鸡群中吃食的特权。
可不要以为小灰只是个有勇有谋的“战斗鸭”,她还是个娱人娱已的 “喜剧鸭”。何婶有一台老掉牙的缝纫机,时不时帮大家缝缝补补干点针线活儿。不知从哪天开始,缝纫机“哒哒哒”的唱歌声和上下起伏的缝纫机脚踏板给了小灰一个天才的创意——趁何婶起身的功夫,小灰大胆地卧在了脚踏板的一端,等何婶再回来踩缝纫机时,感觉又重又慢,低头发现了小灰的把戏,哈哈大笑,跑到院子大声嚷嚷:“你们快来看哈嘛,好笑人喽,嘞个小灰,好会享受哦......”看着一脸惬意地随着脚踏板的上下起伏悠哉悠哉的小灰,她聪明又赖皮的样子逗得我们笑弯了腰。自此,小灰在自创的跷跷板游戏里乐此不疲。
收尾工作琐碎乏味且工资低,大家的兴致都不高。可小灰以一己之力,给平淡的日子添了不少亮色,让指挥部的院子里有了欢声笑语。
小灰虽有强悍泼辣的一面,在小白面前却是个温柔可人的贤妻。我时常在吃饭时将碗中好吃的拨给脚边的小灰,她每次都麻利地用扁嘴叨起来,一边焦急地扑棱着翅膀,召唤小白前来分享,一边还要警惕鸡群的偷袭,手忙脚乱的样子像是在催促:“老公!快来快来!有好吃的!”可往往这个时候,小白老喜欢单独溜出指挥部去外面溜达。
一日午后,何叔提着小白的两只翅膀找到我:“小李,我刚从池塘那边经过,看见小白躺在路边,估计是叫车子撞了。”我一把从他手里夺过小白,轻轻放在地上,仔细检查伤口。小灰则跛着脚绕着小白转圈,叫声急切又凄厉,声音里充满了惊恐和绝望。小白耷拉着头和眼睛,一副生命垂危的样子。抹了红药水和云南白药,仔细包扎了小白受伤的右腿,像是安慰自己也是安慰一脸惊恐的小灰:“么得事,么得事,没有伤到要害,养一阵就能好。”“嘎嘎嘎嘎嘎嘎”小灰不停歇的叫声里满是心疼和感激,一连几天,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小白身旁,也不去何婶那儿玩她最爱的翘翘板了。
过了些日子,小白终于可以摇晃着起来觅食、喝水,只是精神大不如从前,胆子似乎也比以前更小,小灰对她老公的照顾更上心了。右腿受伤后的小白和小灰终于成了天生一对:一个左脚跛,一个右脚瘸,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竟能同频共振,整齐划一,远远望去,像在表演双人秧歌。残疾之后,小白正式收心回归家庭,再不去外面玩耍,对小灰的依恋也与日俱增,走到哪儿都紧紧跟着小灰。小灰终于赢得了她完整的爱情。
我们聚在一起闲聊,开玩笑:“小白被撞,对小灰来说,是因祸得福呢。”
那年,单位在昭通内昆线的工程要收尾了,我被留了下来,听领导的语气,内昆线作为大工程,收尾工作怎么也要个一两年才能结束,让我安心驻守。
春天来了,我在距指挥部两公里的镇上赶场,眼光被一中年汉子的两个筐子吸引——那筐里是毛绒绒、黄灿灿的小鸡和小鸭,它们挤作一团,“叽叽叽啾啾啾”叫声一片,好不热闹。一圈逛下来,汉子那装小鸡的筐已经空了,另一个筐只剩下瘦弱的两只小鸭,其中一只缩在角落里。初春的昭通,风虽不刺骨,但也颇带些寒意,小鸭在瑟瑟发抖。凑近细看,它竟是瘸了左脚的。假装用嫌弃的眼光瞥着那瘸了腿的小鸭,学着当地人老道的样子:“收头不收尾,五块钱,把剩下的这对鸭子给我逮到走。”汉子摆摆手:“算了算了,逮走嘛,不是瘸了腿杆,哪个会卖这么便宜!”两只小鸭,从此正式落户指挥部,成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养的宠物,也成了我的小伙伴。
指挥部饭堂师傅何叔和他的家属何婶是闲不住的人,在指挥部只剩下我们五六个职工后,他们便养了十几只鸡,说要让大家吃上土鸡蛋。鸡们仗着鸡多势众,威威乎,荡荡乎,到处刨食,追逐打闹,好不快活。两只小鸭显得鸭丁不旺,有些找不到组织的恐慌感。不忍心让我的宠物受委屈,我常在食堂里找些吃食,单独找个角落,站岗放哨,让两只小鸭安心进食。
几个月之后,小鸭进入青春发育期,鸭子的食量、块头明显大于何叔两口子养的母鸡了。何婶眼尖,只瞟了一眼,便笃定地给出结果:这对鸭子一公一母,可以凑成一对儿,那只浑身雪白长得乖嘞是新郎,那个瘸了腿杆一身灰毛毛嘞是鸭婆娘。
从那以后,我就好奇地观察起这对鸭夫妇的家庭生活。我管鸭公叫“小白”,管鸭母叫“小灰”。
原以为高大英俊的小白,一定是个“鸭子汉”,事实却正好相反。觅食的时候,鸡鸭有各自固定的食盆。有时,鸡先吃完,就摸到鸭子的地盘想趁机叨上几口。小白总是息事宁鸭的态度,稍微挪动身子,以示默许,小灰则毫不客气地用自己扁扁的嘴巴狠狠地教训那些胆大妄为的来犯者。
小灰并不把母鸡放在眼里,她的劲敌是那只鸡群里的老大——大红公鸡。一开始在正面战场上,小灰没占到多少便宜,但她死缠烂打,愈挫愈勇。更要命的是,小灰善于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几次漂亮的伏击战下来,大公鸡只好偃旗息鼓,装出一副“好公鸡不和女鸭子斗”的姿态,默许了鸭子在鸡群中吃食的特权。
可不要以为小灰只是个有勇有谋的“战斗鸭”,她还是个娱人娱已的 “喜剧鸭”。何婶有一台老掉牙的缝纫机,时不时帮大家缝缝补补干点针线活儿。不知从哪天开始,缝纫机“哒哒哒”的唱歌声和上下起伏的缝纫机脚踏板给了小灰一个天才的创意——趁何婶起身的功夫,小灰大胆地卧在了脚踏板的一端,等何婶再回来踩缝纫机时,感觉又重又慢,低头发现了小灰的把戏,哈哈大笑,跑到院子大声嚷嚷:“你们快来看哈嘛,好笑人喽,嘞个小灰,好会享受哦......”看着一脸惬意地随着脚踏板的上下起伏悠哉悠哉的小灰,她聪明又赖皮的样子逗得我们笑弯了腰。自此,小灰在自创的跷跷板游戏里乐此不疲。
收尾工作琐碎乏味且工资低,大家的兴致都不高。可小灰以一己之力,给平淡的日子添了不少亮色,让指挥部的院子里有了欢声笑语。
小灰虽有强悍泼辣的一面,在小白面前却是个温柔可人的贤妻。我时常在吃饭时将碗中好吃的拨给脚边的小灰,她每次都麻利地用扁嘴叨起来,一边焦急地扑棱着翅膀,召唤小白前来分享,一边还要警惕鸡群的偷袭,手忙脚乱的样子像是在催促:“老公!快来快来!有好吃的!”可往往这个时候,小白老喜欢单独溜出指挥部去外面溜达。
一日午后,何叔提着小白的两只翅膀找到我:“小李,我刚从池塘那边经过,看见小白躺在路边,估计是叫车子撞了。”我一把从他手里夺过小白,轻轻放在地上,仔细检查伤口。小灰则跛着脚绕着小白转圈,叫声急切又凄厉,声音里充满了惊恐和绝望。小白耷拉着头和眼睛,一副生命垂危的样子。抹了红药水和云南白药,仔细包扎了小白受伤的右腿,像是安慰自己也是安慰一脸惊恐的小灰:“么得事,么得事,没有伤到要害,养一阵就能好。”“嘎嘎嘎嘎嘎嘎”小灰不停歇的叫声里满是心疼和感激,一连几天,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小白身旁,也不去何婶那儿玩她最爱的翘翘板了。
过了些日子,小白终于可以摇晃着起来觅食、喝水,只是精神大不如从前,胆子似乎也比以前更小,小灰对她老公的照顾更上心了。右腿受伤后的小白和小灰终于成了天生一对:一个左脚跛,一个右脚瘸,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竟能同频共振,整齐划一,远远望去,像在表演双人秧歌。残疾之后,小白正式收心回归家庭,再不去外面玩耍,对小灰的依恋也与日俱增,走到哪儿都紧紧跟着小灰。小灰终于赢得了她完整的爱情。
我们聚在一起闲聊,开玩笑:“小白被撞,对小灰来说,是因祸得福呢。”